前言:
在德语音乐剧舞台上,《伊丽莎白》屹立三十余年,早已超越“茜茜公主”传奇的再现,成为以音乐与戏剧重述历史、叩问人心的代表作。长期关注音乐剧创作与舞台发展的肖建国,在多年的观演与研究中始终被其深度所吸引。作者认为,《伊丽莎白》既融合古典歌剧的宏大气质,又吸纳百老汇叙事的锐利锋芒,而剧本、歌词米歇尔·昆策与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里维在文本与音乐中探讨的权力、自由与命运,更为作品注入了持久的思想力量。这部作品的核心从不在华丽宫廷,而在伊丽莎白于时代巨浪中不断挣脱束缚、追寻自我的灵魂旅程。
从《我只属于我自己》到死神的象征魅影,再到鲁道夫的悲剧命运,作品以多视角结构拒绝简单定论,将关于真相、偏见与时代枷锁的追问抛向每位观众。
《伊丽莎白》像一封邀请函,引导人们放下浪漫化滤镜,重新凝视那个复杂而坚韧的伊丽莎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自由之光。


1988年,《剧院魅影》首次以德语版在维也纳上演,与之前以德语上演的韦伯作品《艾薇塔》和《猫》一样,译配者依然是德国人米歇尔·昆策(Michael Kunze)。排练期间的一次晚餐上,导演哈罗德·普林斯(Harold Prince)突然拉着昆策灵魂发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写一部自己的原创音乐剧?”

米歇尔·昆策
昆策回答说,他正在构思一个关于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故事。数月后,当昆策将故事大纲和部分歌词展示给普林斯时,故事的主角却已经从皇帝变成了皇后。这也不奇怪,毕竟这位昵称是“茜茜公主”的伊丽莎白皇后名气要远大于她的丈夫。(注1)

1992年,经过多年打磨,众人期盼的音乐剧《伊丽莎白》终于在维也纳上演,虽然它惹怒了保守的评论界,却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彩,并连演多年,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德语音乐剧。这是一部大制作,它讲述了封建帝制的哈布斯堡王朝走向末日的时代背景下,伊丽莎白从15岁入宫成为皇后到60岁遇刺身亡,一生为个人自由而抗争的故事。它不是电影“茜茜三部曲”那样甜美的童话爱情故事,而是严格遵循史实讲述了这位最美皇后悲剧性的人生,毫不回避她的不完美,她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只属于她自己。

该剧诞生以来,以10种语言在14个国家上演,观看人次超过1200万,尚未有其他德语音乐剧能够比肩。
普林斯是百老汇最成功的制作人和导演,能被他期待创作出一部音乐剧的人,也绝非等闲之辈。昆策1943年生,求学期间,他广泛研究法律、历史和哲学并获得法律史博士学位。(学霸相吸,或许国内高校的学霸们爱排他的剧也有这一层原因吧。)但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学者,而是转行进入了流行音乐界并获得更大的成功,作为音乐制作人和词作者,他发现并捧红了许多德语歌手和音乐人,拿到了格莱美奖,坐拥几十张白金唱片和金唱片,名震欧陆。韦伯正是因为欣赏他的流行歌词力邀他翻译了《艾薇塔》,而本来对音乐剧不感兴趣,觉得这种艺术形式老套浅薄的昆策,也在观看韦伯的《万世巨星》等一系列作品后转变了看法。
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一位大师曾在昆策的音乐剧创作道路上亲自引领他前行,被他视为导师,这就是音乐剧之神斯蒂芬•桑德海姆。昆策为《伙伴们》《富丽秀》《拜访森林》等作品译配的德语歌词获得桑德海姆的赞赏。昆策回忆说,桑德海姆教给他最宝贵的一课就是要让观众“意想不到”。

史蒂芬·桑德海姆
创作者有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伊丽莎白》的艺术价值和丰富内涵,它从之前的音乐剧和欧洲的歌剧传统中汲取养分,盛开了更加美丽的花朵,其中既有歌剧式的宏大庄严,艾薇塔式的“旁白+倒叙”框架,也有桑德海姆式的多时空多角度叙事和严肃思考,更折射出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海涅式的讽刺意味,这两位都是伊丽莎白生前喜爱的人物。《伊丽莎白》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万花筒式作品,无论观者是何背景,有怎样的偏好,都可能从剧中获得共鸣。

善于观察的剧迷可能会注意到,音乐剧《伊丽莎白》的各类海报上创作者署名顺序与大多数音乐剧都不同,词作者昆策在前,曲作者里维在后。这是因为昆策的创作方式是剧本先行,音乐必须像电影配乐一样为故事服务。《伊丽莎白》曲作者的寻找一波三折,据说历经三位作曲家,最终昆策还是锁定了自己的老搭档,与他一起获得格莱美奖的西尔维斯特·里维(Sylvester Levay)。他的夫人就是一位研究伊丽莎白的专家,这真是天赐的缘分。
里维是匈牙利人,开始音乐剧创作前,他主要从事流行音乐制作和电影电视配乐等工作。匈牙利是个小国,却产出了诸多优秀的作曲家,里维也不例外。他跳出时代框架的拘束,在《伊丽莎白》的音乐融入了摇滚、爵士、古典等丰富的音乐元素,为音乐剧增添了电影的氛围感,采用音乐动机来表现不同人物性格和处境,既有大量悦耳动听的旋律,剧情需要时也使用一些更大胆的作曲技法,并以恰当的重复再现推动剧情发展,加深观众印象。虽然作曲署名在第二位,但《伊丽莎白》的音乐无疑是它成功的重要保障,众多出圈金曲与剧本相得益彰,构成了和谐的有机整体。

昆策的音乐剧作品总是贯穿着一个主题:个人成长和追寻自我。伊丽莎白正符合这一叙事,她从小在巴伐利亚王国无拘无束地长大,没有像姐姐海伦那样受过严格的皇后训练,与宫廷生活的繁文缛节格格不入,她传世的诗作中常抒发对自由的渴望。
啊,我想造一艘方舟!
在辽阔的大海上,
她壮丽无俦;
“自由”飘扬在她的桅尖,
“自由”屹立在她的船头,
自由的美酒啊,随波泛流。
——伊丽莎白《自由》

剧中开头部分和大部分老套的甜蜜爱情故事一样,皇帝和公主一见钟情,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但很快,“意想不到”的部分接连而来,婚礼上死神搅局预示了这桩婚事的悲剧结局,在婚礼后第二天,看似梦幻的皇室生活也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婆婆索菲清晨就带着侍从前来,从起床太晚说到牙齿丑陋,甚至为未能完成洞房职责而当众责怪她(注2),这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是何等羞辱,更何况透露这一秘密的只会是她的枕边人,当她向皇帝求助时,却遭到冷漠的对待。就在她陷入绝望之时,原本机械喧闹的音乐停止,众人退场,伊丽莎白独留台上,含泪抬头,《我只属于我自己》简洁有力的和弦响起,配合舞台灯光的变换,她仿佛歌词中那只独立而勇敢的海鸥冲向大海,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我只属于我自己》是音乐剧中典型的角色愿望歌(I want song),是主角在逆境之中发出的第一声自由宣言。和《猫》中的《回忆》一样,这首歌也具有让人过耳不忘的特质,不断上升的旋律配合韵脚工整的歌词,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尤其是在女性独立意识刚开始觉醒的国家,更是唱出了很多女性的心声。
这首歌曾被翻译为多国语言,此处选择的是《剧院魅影》作词人查尔斯·哈特填词的英文版。

《伊丽莎白》自诞生以来每次复排都会有一些改动,这首广受欢迎的《当我想跳舞》就是后来加入的新歌,剧中伊丽莎白刚刚与皇帝一同被加冕为奥匈帝国的帝后,登上个人成就的巅峰,但一直跟随她的死神却冷眼看待,两人的唱词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含义。音乐剧中男女声二重唱大多是关于爱情,这首歌却另辟蹊径,节奏铿锵有力,充满矛盾与对抗,张力十足。

死神是本剧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德语中“死亡”是一个阳性名词,所以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拟人化的掌管死亡的神,但通常是扛着镰刀的骷髅形象,如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历史上的伊丽莎白对死亡有种浪漫的渴望,她又狂热地喜爱海因里希·海涅,因此本剧原版中死神的形象像个摇滚明星一样具有魅力,并参考了年轻时的海涅外形。在剧中,死神变化多端,有时是伊丽莎白内心世界的化身,有时又是命运的具象体现,不同制作的演员也为死神赋予了各自的个人特质。本次来京版本的死神演员卢卡斯•迈尔(Lukas Mayer)此前出演过《吉屋出租》中Angel和《万世巨星》中的JC,期待他为死神带来全新的演绎。
历史上的伊丽莎白皇后干政不多,但她在奥匈帝国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源于她一直以来对匈牙利的喜爱,匈牙利也同样对她献上了最热情的欢迎。按匈牙利传统的加冕礼,皇后加冕应在皇帝加冕后几日再进行,这次却为她破例同时举行,伊丽莎白唱出的第一句词是“好一场胜利”。但这真的是胜利吗?死神讥讽地重复“我的胜利”已经暗示了埋下的危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奥匈帝国的建立以及皇后对匈牙利明显的偏袒激化了民族矛盾,加速了哈布斯堡王朝衰落,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但伊丽莎白并不在乎这些,她和儿子鲁道夫都是帝国的叛逆者,甚至作为君主制受益人支持共和制度,就像歌中所唱的“何时跳舞,与谁跳舞,由我一人决定”。
剧中跳舞这一意象常常伴随死神出现,如开场曲中“人人都与死神共舞,却无人像伊丽莎白那样”,以及死神出现在伊丽莎白婚礼上所唱的“最后一支舞,只属于我”。谁能想到,音乐剧爱好者津津乐道的“德奥僵尸舞”竟出自一位美国人之手?本剧原版编舞卡拉罕(Dennis Callahan)按照导演的想法,为亡灵编排了机械而僵硬的舞蹈,反映了封建王朝的严苛与死板,与伊丽莎白跳舞时的活泼灵动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编舞保留至今,虽然是音乐会版演出,观众仍然可以看见这熟悉的舞姿。

音乐剧中设“旁白”的角色由来已久,如《约瑟夫与梦幻彩衣》《拜访森林》中的说书人,《艾薇塔》中的切,《刺客》中的民谣歌手,《汉密尔顿》中的伯尔,这种角色给了作者极大的创作自由,可以将主线故事中无法表现的观点、评价等由旁白说出,丰富叙事角度。

历史上的卢切尼与伊丽莎白的交集仅仅是用一把锥子刺杀了她。音乐剧中他作为疯子和鬼魂,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在《牛奶》《恨》等歌曲中,他毫无顾忌地冷嘲热讽,煽动民众,说出令人不适的真相,反正观众并不需要喜欢他。
Kitsch是第二幕的开场歌,卢切尼在观众席中兜售维也纳街头常见的茜茜公主主题纪念品,kitsch中文常译为“刻奇”,它的原意就是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庸俗艺术品。作者借卢切尼之口嘲讽了近百年来人们只顾着消费茜茜公主的形象,却无人关心事实真相,对第一幕中让观众心醉神迷的伊丽莎白本人,他也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滤镜,指出她是一个卑鄙的利己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这同样是事实,虽然伊丽莎白的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性,她仍然是压迫人民的封建王朝既得利益者之一。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也许所有的书本、影视、包括这部音乐剧都无法说清,昆策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的历史思辨,而里维为他创作的动感十足的摇滚乐是本剧最亮眼的音乐片段之一,结尾的小号华彩和着演员飙高音总是能点燃全场激情。

皇太子鲁道夫是伊丽莎白的儿子,也是她亲手缔造的一个悲剧,是她追求个人自由的牺牲品。在第一幕结尾,伊丽莎白以美貌征服皇帝,赢得了儿子的抚养权,却没有给他关爱,小鲁道夫在《妈妈,你在哪儿》一歌中第一次看见死神,这可以理解为家族精神疾病的遗传,也可以理解为未来的预兆。长大后的鲁道夫与伊丽莎白更加相像,持有相同的政见,与父亲关系日渐恶化,甚至谋反败露,但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伊丽莎白忽视了他的求救(《若我是你的镜子》),于是,儿时的朋友死神再一次造访了鲁道夫,儿子死后伊丽莎白心如死灰,将自己完全封闭,直到死神将她解脱。

《阴霾渐袭》是死神与鲁道夫的二重唱(这首歌名直译是“影子变长”,象征帝国黄昏时分日薄西山的图景),由于梅耶林事件在德奥地区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鲁道夫的结局,创作者们选择将重点放在他的动机上,通过死神怂恿他谋反的过程表现哈布斯堡王朝末日临近之时的社会风貌,沉重而充满压迫感的鼓点和旋律渲染出未知的恐怖气氛,歌词中充满象征主义和暗示,借古讽今,值得细品。
“Zum Klang des Rattenfängers
tanzt man wild ums goldene Kalb herum!
在驱鼠人的笛声中,
人们围着金牛犊疯狂起舞!”
这句词巧妙化用了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和金牛犊的意象,表现了世人在危机下麻木的状态,无论阅读多少次,还是令人拍案叫绝。

作为伊丽莎白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本剧中并没有多少存在感,甚至没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独唱,在朝廷,他听命于母亲索菲,虽怀有残存的仁爱之心却只能实行冷酷的高压政策,在国际事务上举棋不定昏招频出,在后宫,他虽崇拜伊丽莎白,但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注定不幸,皇帝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她,甚至还给了她难以启齿的疾病,二人也渐行渐远直到阴阳两隔。

《暗夜之舟》是夫妻间最后一次二重唱,这首歌的曲调与二人定情时所唱的《世上无难事》一模一样,仅结尾不同,却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曾经虚幻的幸福化成如今真实的悲哀,令人唏嘘。
以上选取的仅是《伊丽莎白》中的主要人物和最受欢迎的几首歌,但《伊丽莎白》无废曲,剧中动听的歌曲远不止这些,剧中配角也都有名字和历史背景,受篇幅和其他原因所限,无法在此一一介绍,有待读者去自行发掘。
注1:关于《伊丽莎白》的诞生时间说法不一,此处仅为Kunze在英文采访中给出的一种解释,读者可自行判断.
注2:这些细节都是历史上的真事,伊丽莎白因为牙齿的缺陷几乎从不大声说话,留下的照片也没有露过牙齿。——参考自哈曼:《茜茜公主:伊莉莎白(一位不情愿的皇后)》
作者:肖建国
编辑、排版:赵萍萍
备注:
-
德语原版音乐剧《伊丽莎白》音乐剧版音乐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剧照摄影 李晏、王小京
-
演出阵容以实际为准
相关阅读:

德语原版音乐剧《伊丽莎白》
音乐剧版音乐会
演出信息
演出地点: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演出场次:
2026年1月28日(周三)19:30
2026年1月29日(周四)19:30
2026年1月30日(周五)19:30
2026年1月31日(周六)14:00
2026年1月31日(周六)19:30
2026年2月1日(周日)14:00
2026年2月1日(周日)19:30
票价:
1080/880/680/580/480/280/180元
购票二维码:

《伊丽莎白》购票二维码
















登录/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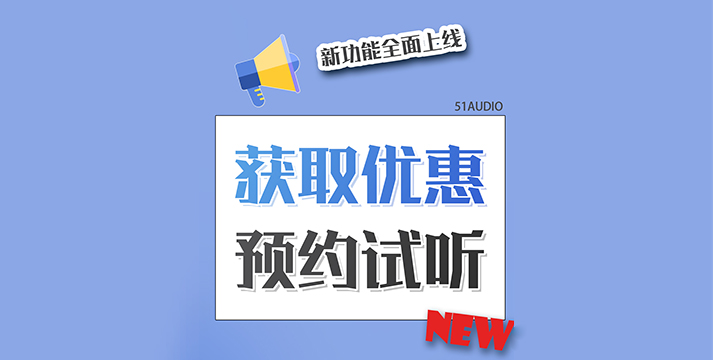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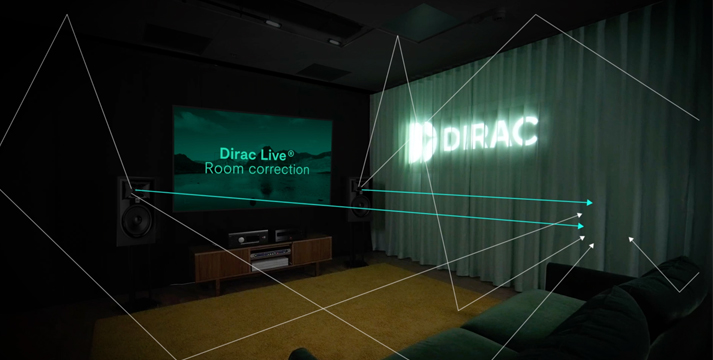

©2019 51audio.com| 京公网安备 11011102002095号|京ICP备20003013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4178号|京网文【2020】4008-712号|经营许可证编号:京B2-20203036

 中乐之声
中乐之声